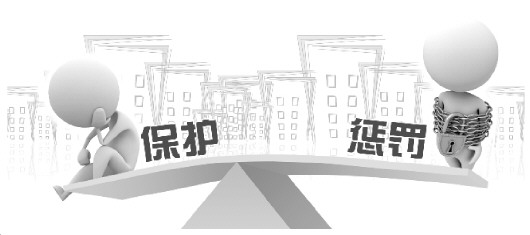
制图/李晓军
□ 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宁宁
10月3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为期一个月。
此前,从修订草案10月21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之时,有关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该如何量刑处置的讨论热度一直持续至今。眼下,热门电影《少年的你》更是引发了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前所未有的关注。
近年来,未成年犯罪暴力恶劣案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低龄化趋势,犯罪的动机、手段、方法越来越倾向于暴力化、多样化,犯罪的群体和规模不断扩大。因此,有观点强烈建议降低14岁刑事责任年龄。但与此同时,也有观点主张对“严刑重典”应该谨慎,惩治未成年犯罪不能只依靠刑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不是万能法宝,这种做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究竟能起到多大的正向作用,本身就值得考虑。
未成年人保护和惩罚之间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
设计合理有效惩戒制度是关键
实际上,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统计数据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的态势是犯罪率有所下降,但绝对数量仍居高不下,甚至有所反弹。有研究表明,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主要来自五个方面,即不良社会环境、不良家庭环境、不正确的教育方式、权益保护不到位、自控能力较差。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有64名全国人大代表领衔或联名提出关于修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议案两件。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有92名代表提出修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议案3件,31名代表提出制定少年司法法的议案1件。
全国人大代表陈海仪是一名专门从事家事审判的法官,被称为“法官妈妈”。代表履职过程中,她提出的建议都是与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相关的。在她看来,这些孩子身上普遍都存在着“三难”,即家庭难养、学校难教、社会难管。因此,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实际上是个系统综治的工程,不只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
“现在前沿的解决机制是缺失的。修订草案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职责的划分,但是却没有具体工作由什么部门来承担。”陈海仪建议在机制构建上进行完善,此外,国家应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统计调查制度,开展未成年人状况统计、调查和分析。
全国人大代表符宇航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加强对未成年人涉罪分级处理的建议,希望能够把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12岁,对于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按成人的法律来执行。同时,她还建议恢复收容教养制度,增设收容教养机构即从前的工读学校。
“草案第三十九条规定,从专门学校决定转回普通学校就读的,其原所在学校不得拒绝接收。如果这种学生行为危害特别大,经教育也不容易被转变,转回原学校还会有潜在危险,学校和家长愿不愿意接收他回到校园?应当有一种商议的形式,而不是强制学校来接收。”符宇航说。
专门学校相关规定亟待完善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多为指导性倡导性条款;针对应当重点预防的九种“不良行为”,法律规定了19条处置措施,其中不少内容可操作性不强……
显然,预防措施不给力,是现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律体系的一大缺陷。
现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于1999年颁布实施,是依据上世纪末我国基本国情制定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为动员全社会开展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该法规定的预防思路、预防手段和处置措施等,明显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已影响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顺利开展。
更值得关注的是,针对需要矫治的九种“严重不良行为”,法律规定了4项措施,即监护人和学校严加管教、送进专门学校、公安机关予以训诫、政府收容教养。这些措施中“以教代罚”的措施只有送进专门学校一项。
实际上,“以教代罚”才是真正有效的预防措施。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此次修订草案明确了需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或教育的情形,但就专门学校并没有作相关具体规定。鉴于此,多位委员建议要进行补充,以便于社会对专门学校有更清晰的认知。
“要下大气力办好专门学校,加大投入,加强管理,切实解决机构、编制、经费、管理办法等相关问题,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矫治提供实践可能。”邓凯委员说。
李钺锋委员也建议在修订草案中对专门学校的性质、主管部门、工作职责以及专门学校的设置、管理进行明确,同时,还要对有权决定送专门学校的部门加以确定以便于实践操作。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实践中,一些父母尽管知道自己的孩子已具有不良行为,也不愿意送到专门学校矫治。鉴于此,杜玉波委员建议规定专门学校特殊情况强制入学制度。“中办国办的意见中已经明确规定了特殊情况强制入学的相关内容。修法时要与这个意见相衔接,以解决家长不情愿的问题。”
修订草案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严重不良行为情节恶劣或者拒不配合、接受本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教育矫治措施的未成年人,可以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专门学校可以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采取必要的约束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矫治。
“约束措施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决定?从法律条款来看,约束措施已经超过矫治和接受教育的范围,其本质接近于收容教养。”吕薇委员认为,是否采取约束措施应该由专门学校自行决定,建议参照矫治措施由公安部门来决定。
修订草案第三十八条规定了对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送专门学校的程序。为进一步完善进行教育矫治的未成年人送专门学校的程序,提高评估决定的科学性、严肃性,李锐委员建议将本条第二款修改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建议或者申请,组织教育学专家、心理学专家、未成年人社会工作者专业人员进行评估,依据评估结果作出决定”。
“修订草案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之间是什么关系?具体评估哪些因素?”吴玉良委员建议在法律里或者将来在配套规定中对送专门学校的条件讲清楚,否则教育行政部门不好作决定,家长对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也不好掌握,容易引发争议。
他山之石可否攻玉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也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同难题。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缔约国应当规定最低的年龄来追究刑事责任。各个国家和地区可以根据自己本国情况,来确定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的起点。
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采用辨认和控制能力与刑事责任年龄挂钩的做法。从19世纪末开始,把未成年人当作特殊的群体加以看待,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特殊机制。比如,美国成立了青少年法庭,采取所谓的国家亲权主义思想来对待。再比如,英国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恶意补足年龄”的处理方式,即7岁至14岁的未成年人青少年犯重罪,如果可以拿出证据证明其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那么即使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也照样可以追究责任。
那么,在立足本土的前提下,这些做法在中国能不能实施呢?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新看来,非常困难。“这种做法是与英美判例法土壤相结合的,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具备实施的条件,因此不能照搬,但这种思路可以借鉴。”王新说。
“对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必须多管齐下,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修法的重心应放在对未成年人保护大的政策背景当中进行综合治理,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惩罚打击上。”王新认为,对于预防和惩治未成年人犯罪来说,发挥社会、学校、家庭本身的职能、完善和修改未成年人犯罪事前事后处置机制更为重要。对未成年人的处罚,不能完全按照成年人刑事责任追究的模板来进行,而把其他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而对于目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强烈呼吁,王新则认为需要非常慎重理性。“现行刑法把14周岁作为刑事责任追责的起点是符合心理认知普遍原理的。刑法中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需要考虑主观恶性,前提是要考虑到他应该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但是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认定起来因素比较多。”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仿佛把青少年罪犯纳入到打击圈内就可以一劳永逸。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大家有可能把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只归结到个体上,忘记了根本原因。社会、家庭、学校,这些外围的因素才恰恰是更重要的,并不是简单地关进监狱就可以解决。是否需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需要进行深入调研,征求全社会的意见,并按照法律修订程序来严格操作。”王新同时强调,时代在快速发展,未成年人犯罪确实出现了新的形态,有一些小孩是少年老成的,虽然他没有达到14周岁,但他的辨认控制能力和成人一样。针对未成年人立法需要与时俱进,应当适时作出调整。“但这种调整一定要从对未成年人保护政策的角度出发”。